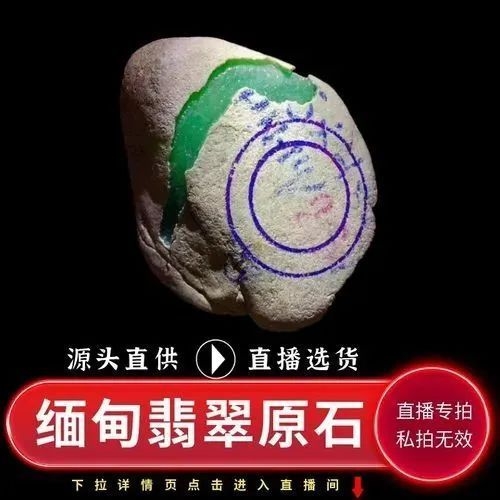““一轮明月照乾坤,茫茫大海并不深。日行千里身不动,两脚悬空赛神仙。”
这是老北京玉雕行流传的一句顺口溜,刻画了传统玉匠们的工作状态——终日坐在“水凳”上操作,靠脚蹬提供动力(略似健身用的动感单车),带动砣具磨玉。一天下来,双腿运动多,却“身不动”“两脚悬空”,对裤裆的磨损较大,有“好女不嫁磨玉郎,日日夜夜守空房。有朝一日回家转,补了袜子补裤裆”之说。
治玉的主要工具是砣具(即“一轮明月”),种类甚多:铡砣开料,錾砣粗雕,钩砣刻线,轧砣、钉砣细雕,冲砣磨平,碗砣磨碗,膛砣磨内膛,弯砣掏膛,磨砣制珠,胶砣、木砣、皮砣和毡砣抛光……
老北京玉雕作为老北京美术“四大名旦”(另三为漆雕、牙雕和景泰蓝)之一,曾涌现出姚宗仁、邹景德、潘秉衡、刘德瀛、王树森、何荣等大师,文化积淀深厚,惜今人知之甚少。

潘秉衡玉雕作品《火龙驹》近日,电视剧《宣武门》开播,讲述了老北京玉雕艺人李天顺保护国宝玉器的故事。查清后期造办处记录,玉器作未见李家;李天顺磨玉,竟直接在桌上操作;剧中对玉器行规矩的呈现较少;慈禧太后是在中止“百日维新”后,才知康有为、谭嗣同的“围园劫后”之谋,剧中搞错了时间顺序……
电视剧是艺术创作,不必纠缠细节。《宣武门》故事发生的背景,值得钩沉。
元朝玉匠聚居广安门
中国玉史悠久,河姆渡文化(距今5500—7000年)的玉璜、龙山文化(距今5500年)的玉龙、良渚文化(距今4300—5300年)的玉琮等即为明证。甲骨文中有“玉”字,周代设专门机构“掌玉瑞、玉器之藏”。
自元朝起,北京成全国政治中心和手工艺制造中心。中统二年(1261年),元朝在北京设金玉局,至元三年(1266年)改称总管府,其中“玛瑙玉局”负责治玉,另有“玉提举司”“玛瑙提举司”“瓘(音如冠,一种玉器)玉局”,亦掌治玉。
元重手工业,忽必烈在北方“括其民匠,得七十二万户”,灭南宋后,又“籍江南民为工匠,凡三十万户”,编入匠籍(世代服务官府,不得脱籍),入宫作劳动,玉匠亦在其中。《元史》称:“国家初定中夏,制作有程。凡鸠天下之工,聚之京师,分类置局……故我朝诸工制作精巧,咸胜往昔矣。”北京治玉水平陡升。
传说治玉祖师爷是丘处机,据说他“掐金如面、琢玉如泥”,西行见成吉思汗时,学会西域的相玉、琢玉技巧。《白云观玉器业公会善缘碑》(立于1932年)称:“(丘处机)慨念幽州地瘠民困,乃以点石成玉之法,教市人习治玉之术。”在老北京,会念《水凳歌诀》的道士,就会得到玉匠招待。据说丘处机先传治玉,后收道门弟子,故道士称玉匠为师兄。
元代玉匠住在哪?据元熊梦祥《析津志》载:“南城彰仪门外,去二里许,望南有人家百余户,俱碾玉,是名磨玉局。”彰仪门即今广安门,距宣武门不远(约2.2公里),当时最顶级的玉匠“俱西域国手”。
明朝“苏琢”更胜一筹
明朝时,宫廷玉作归御用监管理,御用监职责是“凡御前所用围屏、床榻诸木器,及紫檀、象牙、乌木、螺甸诸玩器,皆造办之”。
明朝重和田玉,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》中称:“凡玉入中国,贵重用者尽出于阗、葱岭。”学者王君秀考证,因无法有效管控和田玉产地,“宫廷治玉的玉料获得主要是靠朝贡和贸易两种管道”。《明史》载:景泰七年(1456年),撒马尔罕贡玉,“堪用者止二十四块,六十八斤,余五千九百余斤不适于用”。
当时苏州治玉水准最高,宋应星说:“良玉虽集京师,工巧则推苏郡。”
自明代起,苏州以阊门为中心,在专诸巷和吊桥一带,出现200多家玉作,称“苏琢”,奉周宣王为祖师爷,建有周王庙。周宣王是西周第十 一 代 君 主,启“宣 王 中兴”。一次大旱,他舍玉圭祈雨,《诗经》中记为“圭璧既卒,宁莫我听”。
“苏琢”有名师陆子冈,或嘉靖、万历年间人。据《太仓府志》:“五十年前,有州人陆子刚(冈)者用刀雕刻,遂擅绝,今所遗玉簪,价一支值五六十金,子刚死,技亦不传。”陆子冈是首位在玉器上落私款的匠人,他所制玉牌闻名,即“子冈牌”。据说他有独门刻刀,名“昆吾”,从不示人。
明代王世贞在《觚不觚录》中称:“(陆子冈之作)皆比常价两倍,其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,近闻此好流入宫掖,其势尚未已也。”传说万历皇帝招陆子冈入宫,命他制玉壶,他把名字偷刻在壶嘴中,后遭人告发,被诛。
明代玉雕被称为“粗大明”,粗犷、宽厚,细节常不足。
清宫玉作匠人难发挥
清代宫廷玉作归造办处,初期在故宫养心殿,至迟到乾隆十三年(1735年)时,圆明园、故宫均设“如意馆”,且苏州、扬州、江宁、淮关、长芦(后迁至天津)等八地设官玉局。无官派活计,匠人可自行生产,仍有官粮可领,即“停机养匠,以备传奉活计”。
据杨伯达先生《清代宫廷玉器》一文钩沉:苏州治玉胜在精巧,乾隆赞为“相质制器施琢剖,专诸巷益出妙手”,称苏工“精练”,京工“草率”;扬州治玉以大取胜,整玉雕成的山水景观“玉山子”,多送扬州,代表作是《大禹治水图》,重达5吨。
宫作则人才不足,玉匠多来自南方。杨伯达先生从档案中,钩沉出杨玉、许国正、陈廷秀、都志通、姚宗仁、韩士良、邹学文、黄国柱、施仁心、陈宜嘉、王咸、鲍友信、顾规光、倪秉南、周云章、张家贤、朱彩、金振寰等南匠。宫作分南匠、北匠和八旗家内匠。
南匠“每月食钱粮银四两,每年春秋两季衣服银十五两”,旗人仅二两。南匠分传差南匠(临时招来,事毕可还乡)、供奉南匠(长期服务,退休后还乡)和抬旗南匠(隶内务府,永不归南)。显然,《宣武门》中李天顺的祖上应是抬旗南匠。
北匠中有和田人,乾隆不太欣赏他们:“和阗(今作田)虽有玉工,而不能精琢。”
宫作与苏州、扬州鼎足而三,技艺却稍逊,或因皇家管得太多。雍正说:“从前造办处所做的活计,好的虽少,还是内廷宫造式样,近来虽甚巧妙,大有外造之气,尔等再做时,不要失其内廷宫造之式。”扼杀了发挥空间。
皇帝给匠人撑腰
《宣武门》中,李天顺敢跟宫廷卫兵叫板,甚至不惧崔太监,未必是夸张。清代皇家对玉匠较宽容。
雍正曾下旨:“如匠人有迟来、早散、懒惰、狡猾、肆行争斗、喧哗高声、不遵礼法,应当重责者,令该管人员告诉尔管理官,启我知道再行责处,不许该作柏唐阿(满语,意为执事人,无品级)等借公务以报私仇,擅自私责匠役。”管事的无权直接处分匠人。
乾隆也偏袒玉工,他最欣赏姚宗仁,撰文说:“宗仁虽玉工,常以艺事谘之,辄有近理之谈,夫圬(音如污,圬者即瓦匠)者、梓人(木匠、刻字工)虽贱役,其事有足称,其言有足警,不妨为立传。”姚宗仁是苏州人,也是抬旗南匠,在宫中服务了24年。
传统工匠均称“师傅”,唯玉匠称“先生”。传说乾隆曾得一块好玉,便定了题,要求按期完成,玉匠认为题与料不符,遂怠工。乾隆怒责,玉匠申辩说,按题制作,玉就毁了。乾隆大悟,此后不再定题,玉匠自行问料、自行设计,遂称“先生”。
清帝中,乾隆最喜玉,他在位时,和田每年贡玉4000斤,其实常超此数。乾隆禁止私人贩运,否则“照窃盗例计赃论罪”,目的是牟利。他将玉分成五等,一等宫中用,二等每斤银一两三钱,三等银一两,四等银八钱,五等银六钱。
然而,民间走私难止。乾隆下江南时,见“苏扬玉肆率多精璆(音如求,美玉)”“一望而知为和阗之产”,但禁不胜禁,只好装看不见,“知其为窃卖而不深禁也”。
嘉庆时国力衰退,虽贡玉数量未减,但已很少做大件了。
“青山居”崛起
1821年,道光皇帝登基第二年,停贡玉,杭州等地官玉局亦停办,至清亡未再恢复。慈禧太后时,宫廷玉作“回光返照”,据杨伯达先生钩沉,圆明园被毁后,只剩故宫北五所最西一所院落,工匠锐减,档案中仅记周文元、周昆岗两名玉匠,无李家。
慈禧太后喜玉,“主要是向织造、钞关索要”,光绪皇帝登基需35方印,交苏州织造去刻,3年后才将玉料呈览。
宫作衰落,民作崛起。
光绪初,崇文门外北羊市口有黄酒馆,号“青山居”,附近大栅栏有珠宝市,“红货行”(珠宝玉器行业)商人上午10点到此交易玉器,下午即散,朝鲜、日本、美国等国商人也来此。
此前玉器行多“内局”(不在门市交易),1922年,一名叫李敬轩的商人牵头,买下附近地面,改建成玉器市场,近1000平方米,200多摊位,回族商人居多。据李伟的《抗日战争中的回族》:“(旧京玉器行)从业人员2000多人,其中回民占70%以上。”
学者苏欣在《京都玉作》中认为,老北京玉器行“袖内拉手”的交易方式,可能就来自西北“掏麻雀”的习俗,此外,“牙齿当金使”,不立字据,全靠口头承诺,也是回民珠宝古玩商的规矩。“翡翠大王”铁宝亭就是回族商人,他已是百万富翁,每年农忙仍回乡务农,因他的父亲要求,既经商也要种地。
写老北京玉器行,也许称《崇文门》更合适,崇文门附近玉匠多,但也有不少生活在宣武门附近,比如牛街有“寿面刘”,擅做玉鼻烟壶,烟壶两耳称“寿面”,故有此称,他收徒弟18人,影响颇大。
太多故事还没讲
老北京玉器行文化积累深。
据学者苏欣钩沉,玉器行规矩森严,车间“三不许”:不许大声喧哗;不许随意窜车间,不许随意窜凳,不经允许严禁动别人的活;不许放音乐。
治玉大师李博生说,传统车间让人“觉得很神圣,很有殿堂的感觉”。同事间严防偷艺,做一半,暂时离开时,玉匠会在半成品上撒一把沙子,如被偷看,能迅速发现。
玉行“同行不串门”,别家“先生”到访,“了作的”(作坊主管)立刻带开。被允许进玉作坊的人,进门后要背手,表示不会偷料,参观时远离水凳。到店买玉器,掌柜送客到库头(仓库门口),会背过脸去,因门口会放一些小件玉器,供客人免费拿,但“只能送,不能偷”,偷窃者无法再混玉行。
“夹包的”(又称“包袱斋”)串玉坊收购,他们靠眼力吃饭,一位“夹包的”给李博生留下印象:“他一去世,所有做玉的人都觉得惋惜和遗憾,因为感觉没人欣赏自己的东西了,有真本事的人没了。”
民国时期,老北京玉行涌现出“四杰”,即“大大咧咧是何荣,惹不起的刘德瀛,王树森是小诸葛,臭要饭的潘秉衡”,技术出众,生活却艰难。以“四杰”之首潘秉衡为例,他曾在北京大学夜大学习一年,后复原了失传多年的“玉器薄胎金镶玉”技艺,名噪一时,可品珍坊倒闭时,不得不携子女沿路乞讨返乡(河北固安),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,生活才有着落,安心研究技艺。
老北京玉器的故事数不胜数,《宣武门》开了个头,希望未来有心人能更深入去挖掘。
责编:沈沣